
图源:受访者
撰文 | 张圜
编辑 | 柳逸
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?这是宫崎骏《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》中,神对孩子发出的天问。在哲学家眼中,更多时候,这是一个关于选择的议题,而对许多普通人而言,这个问题的答案只有在历经困苦与宿命之后才会到来。对作者杨海滨而言,写作非虚构的过程,就囊括了一个又一个这样的选择。
1996年,父亲去世数年后,母亲也已病重。杨海滨从北京回到河南温县老家照顾母亲,准备药物,洗衣做饭,料理家中事,陪母亲聊天。那段时日,空闲时,他开始整理思索,回溯过往,一种隐秘念头,从心底冒出。上世纪八十年代,因求取事业升迁的念头,杨海滨主动调离了青海牧区,辗转西宁、武汉、北京,最终回到平原上的郑州工作。从那时起,他离开了自己从小生活的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班玛县。对当时年轻的他而言,这是一个好选择,他选了平原,它意味着更有上升空间的职场环境,更丰富的生活条件。但当时间行进到那段闲日里的某一个节点时,他忽然发现,生活步入了一个可以回溯并再次迈步的阶段:关于青海,关于果洛,藏地的回忆,这一次,他要选择开始写了。
2019年,在镜相栏目开设非虚构专栏“藏地往事”以后,杨海滨陆续将自己在藏地牧区生活的见闻回忆整理了出来,他的笔下,有牧民、藏区司机,还有挖虫草的农民。2020年以后,他又写出一系列平原故事,写河南的“新朋友们”。病毒肆虐时仍给社区老人送菜的郑州快递小哥贠社起,温县太极拳大师陈照丕,豫北村官马国力,还有热爱考古、精准定位曹操墓位置的安阳农民龙振山……出现在杨海滨文章中的所有人,都有个共同点,他们都是普通的、不起眼的人。
接受这次采访时,杨海滨又一次回到西宁,寻访一位旧日友人进行采写。离开青海多年,他仍不断回乡采访、又回到平原,在各地奔波找寻素材,写完后又开始下一篇的酝酿,细碎漫长的写作之路,种种决定似乎已经拼合成一种完整的习惯。
“如果可以的话,我应该要留在青海生活的。”问及写作之路的缘起时,他毫不犹豫地回答。无数次离开又回归,他不停地奔走在朝向高原的一条路上。上世纪五十年代,杨海滨的父母从老家河南出发,到青海支边下乡建设,搬到了果洛,他也因而在边地出生,自幼以胡儿语为母语。
如今,时间过去七十年,在他的视界里,回忆的路途与风景是怎样的?
今年春夏,杨海滨的新书《在阿尼玛卿脚下》出版,专栏“藏地往事”系列文章收入书中,终于形成一段完整的生命故事。书中写着奔腾而过的黄河,封山季放牛人壶里的青稞酒,杨海滨的青春回忆中,果洛县城从未老去,故事中的人却几多移换。聚散是草原上牧人的换季,生死不过是雪山脚下藏民的日常。
而写尽生死之后,自己又要朝向哪儿去?关于这个选择,我们与他深入聊了聊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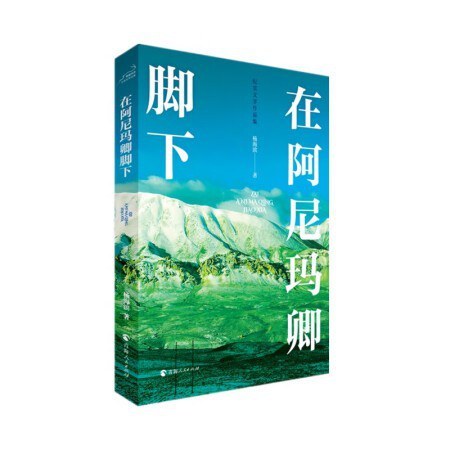
《在阿尼玛卿脚下》(杨海滨著,青海人民出版社,2025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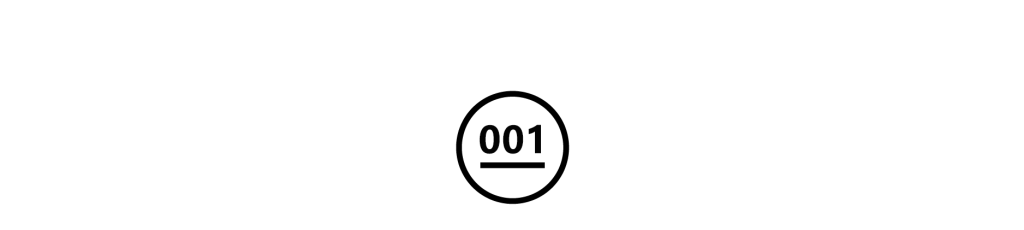
命运如纸鸢,“死”也很平常
镜相工作室:
你在澎湃新闻镜相栏目开设的“藏地往事”专栏已经更新多年了,能否简单谈谈你所知道的果洛,当地藏民的生活方式与我们生活在城市深处的人有什么不同?
杨海滨:
差别非常大。城市的人对于生死大多很忌惮,希望回避谈论这个问题。我是从藏地出来的,在当地长到了30多岁才离开,到平原地区跟他们谈起生死的时候,大家一脸严肃。在牧区谈论生死,其实和谈论喝茶一样,是很平常的话题。
当时我和一个藏族同事,我们每一年都要下帐——下乡到农民的家里,九十年代前,高原的交通非常闭塞,有些地段根本就没路,我们要在原始的高原上行走。有天早上,这个同事要远去巴颜喀拉山附近的一个大康公社,去下帐。他早上走时,围绕着我们单位的土坯房,开玩笑地喊:“朋友们,我的兄弟们,我要走了,我要跟你们永别了!”
藏族人把死看得很平淡,他认为自己也许出去就真的回不来了。
后来,他有次下帐,骑着马渡过玛可河边的一条小路,马一打滑,他真的就掉到黄河里淹死了。死对我们就是很平常的一件事。
我再举个例子。班玛县离西宁有将近八百公里,中间有几座雪山,比如说阿尼玛卿雪山,都是很高大的,冬天去办事,必须坐便车,交通非常不方便,想从班玛县到西宁去一趟,你需要费很多心机,给司机准备好吃的喝的用的,所有的东西,才能搭车,三天以后才到西宁。
班玛每家人都有很多只牦牛,冬季山路很滑,车走在半路,如果突然一头牦牛脱队跑到路上,一个猛刹车,整个车都容易打滑滚到山脚下。站在山的公路边缘,往下看,过去的事故汽车就像一块块小黑点。因为死亡经常发生,当地人对死亡有种从容的态度。与其他地区相比,生死观差异还是很大的。
1954年建成的班玛县,整个县城的规模只相当于北方一个中等大小的农村,居民不超过500人,人少,人和人之间就特别真诚,说话都直截了当。从青海调到郑州后,我在单位里无法用在青海时候的方式对待河南人,文化的差异特别大,我当时觉得我无法适应这里的人际关系。这也是我很早就离开那个单位的原因。
镜相工作室:
您开始写作之初,有遇到过什么困难吗?除了藏区故事,后来您也一直在书写河南人,回到河南生活之后,也记录着新地方的寻常生活故事,这种焦点的转变顺利吗?
杨海滨:
这个问题还是很伤感的。我写青海故事的时候,看着从前我父亲的故交们慢慢死去。他们以前看着我长大,我非常了解他们,好像闭着眼睛就能看得到这一大帮的人。我30多岁离开青海,我写的时候又过去了30年,这些人早已化作果洛天上的白云了,在我这个心灵里一直飘着。我无法再和他们说话了。
我也会回到青海,寻找我父亲的那些还健在的老同志,进行采写。有时候,我也会直接打个视频电话,微信采访,昨天晚上我又到西宁来了,也是来采访一个人。我得不断出行,换各种交通方式,克服距离的不便,有时候还有其他尴尬的问题。但总而言之,不断采访、写作,就是一个爱好,我也收获了很多。
有时候我觉得当时回郑州是一个错误的选择,我应该继续留在青海的。在牧区,写作会更顺利。我毕竟对那儿的生活很熟悉,到了郑州,不适应,又离开了单位。后来受到编辑们的鼓励,我也尝试去找一些身边的小人物、新朋友们:月嫂,村长,打太极拳的。除了写青海,我还愿意去了解一些边缘的小人物,他们非常淳朴,都很愿意跟我聊,这也是我尝试了解他们的生活的原因。
镜相工作室:
不断出发、采访、写文章,对于很多写作者而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,你是怎么支撑自己“全职写作”的?
杨海滨:
我在果洛的时候,在银行工作,后来调到了西宁市里,又从市里调到了湖北省,最后借调到北京总行,父母年纪大了以后,我回到了郑州市的银行工作。我是2000年左右离开银行的,但我一直交着社保,退休后还有点退休金。我不抽烟,不喝酒,不做生意,费用也就是勉勉强强够用。写作这个爱好是我生活很重要的调剂。
镜相工作室:
生活在大城市的受访者们,很多是不是边界感会很强?比方说受访者们会不会更内向,谈起自身生活经历时更谨慎?想听您聊聊这之中的一些有趣经历。
杨海滨:
采访当中啊,那真是一言难尽。有很多很伤脑筋的事,有的选题拟好,我甚至准备就绪,要买票去青海了,受访者们这边就突然会出现问题。比如青海格尔木市那边,是个石油重镇,那儿有个很优秀、很有意思的四川女工。她年轻时从四川流浪到青海,最后成为了车间的党支部书记。我觉得这个故事是可以写一写的,但是约她的时候她同意,真的要写,就不同意了。那个女工说,你一写,我岂不是就像贪官污吏一样被曝光了?他们思想确实可能会相对保守。反而是在河南,我之前采访的我身边的小人物,月嫂、牛肉店老板,他们会很真诚地给你讲自己的故事。
我还有一个困惑的问题,就是语言。
彝族诗人吉狄马加,他的一个朋友是青海师大英语系的教授,姓黄。我看过当年他们一起做过的一部纪录片,讲二三十年以前,一个美国人拿着天主教会发给他的500万美金,到藏区建立学校的故事。这个学校当时旨在给牧民的孩子提供学习机会,算是对中国的文化投资。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题材,我从吉狄马加那里知道了这件事后,就想采访这个人。
我把这个想法说给黄教授以后,他非常支持,跟美国人联系了,把联系方式也给了我。但我正面临一个问题,语言的问题。我是草原上出生成长的,我不会英语,而那个美国人汉语非常蹩脚。
我是一个民间的写作者,说好听点,一个自由撰稿人,一切采写所需费用常常都需要我个人来支付,不像大学教授,有经费,我没有。我也没有记者证。我一直想去云南采访这个美国人,邀请他讲讲他在中国牧区帮助牧人孩子接受教育的事。但我负担不起翻译的费用。我有时候面临的困境,是各式各样的。
我们民间的写作者,其实是比专业做新闻、文学的人要艰难。在我看来,写作本身不是问题,问题是怎么找选题,怎么找到受访者,这才是目前对我来说比较困难的事。

图源:受访者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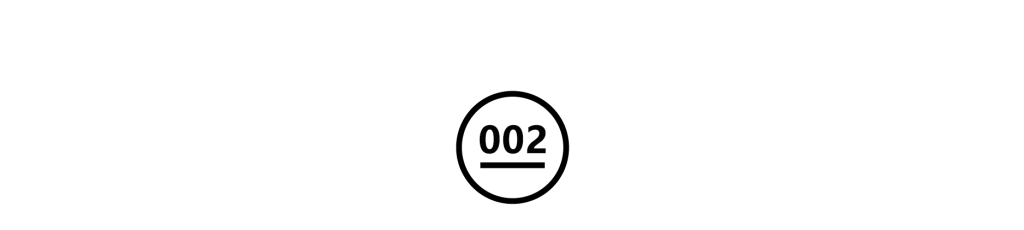
“想起写过的人物,我还是会掉下眼泪”
镜相工作室:
您在《在阿尼玛卿脚下》第一章提到,在雪山脚下遇到一次山难之后,你获救时想到阿尼玛卿之外的大陆,西宁、郑州,还有许多我们经历过并将要经历的生活,两种生活的极大反差让你“觉得很不真实”。在河南的生活和整个青春时代在藏区的生活,有什么巨大的不同吗?你与青海的藏民们的生活也有众多交集,在你眼中,他们的人生是值得过的吗?写他们的故事,对你自己的生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?
杨海滨:
毫无疑问,我喜欢藏区的生活。那里毕竟是我的出生地。是我的初恋,也是我事业成长的地方,假如我不离开那个地方,我的事业、生活都会更好,我会进步得非常大,但是命运有时候就像风筝纸鸢一样,飘到哪你不能确定,命运不可自主。
我觉得我这一代人的命运和我父辈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,他是从中原来的第一代移民,他的漂泊命运注定了我这一辈的流浪。如果他们不去青海,我可能会在河南出生,我会和很多年轻人一样,接受很好的教育,然后有很好的工作。但正因为他去了青海牧区,我才会长到13岁才第一次吃到橘子。
那一年,阿坝县跟班玛县之间的公路修通了,有人买了一车四川产橘子,拉到班玛县,他们开始分,我不知道这是啥东西,一次吃了五斤。后来我父亲才告诉我这是橘子。
班玛县太闭塞、太艰苦了,我小学的老师教我们念书时说,“向张海迪阿姨学习”,她不认识那个字,就胡念,念“张海由”,那个时期牧区的教育质量非常差。当时,我们这一辈的年轻人都觉得,果洛这么艰苦,就都想调离那个地方,想回到西宁或者回到内地,我也不例外。所以我当时拼了命去西宁。
我调任到西宁时就已经开始写作了,只不过当时只是散落地写一些私人的回忆,不像今天,写成一个个完整的故事。
“我的藏族叔叔阿拉旦巴”这一章节的故事就是个例子。我这个叔叔1958年被诬陷叛乱,被判了无期徒刑,我父亲帮助他平反,他在狱里待了十三年,八十年代才平反。八十年代之后,他觉得青春已逝,就用补发的十八万工资疯狂挥霍,买酒喝。酒这个东西,藏民都爱喝,因为天气冷。但他喝酒逐渐成了瘾,最后喝到去医院抢救,清醒过来以后看见桌子上有一瓶酒精,他又把那个酒精喝掉,然后就死了。
我父亲让我帮叔叔办一场天葬。来天葬的兀鹫吃了他的身体以后,甚至飞不起来了,醉了。天葬师把自己喝的茶水倒在碗里,抱起那些兀鹫一个一个喂,过了好久它们才清醒过来飞走。在青海,这类的奇异故事很密集。像这样的事,我多年之后才能把它写成一个故事的模样。
写了这么多以后,我现在常很忧伤。想起他们,就很忧伤。人生的意义我说不清楚,但是我有一种感受,就是我所写的这些人物身上都充满了忧伤,甚至想起他们的时候,我还会掉下眼泪。
我越写,就越会感到困惑,生命的意义何在?我经常想起这样的问题,我们活着难道仅仅是为了承受这些苦难吗?
当然,也有快乐的时候。比如我中学时代的初恋,我跟一个女孩子在草地上坐着,看着遍地的野花,看着成群的鹰隼,那也是一种动人的,让人永远不能忘记的时刻。但是更多的时候是无奈、痛苦和失望。
镜相工作室:
总的来说,您写过的所有人身上都有着一种专注、纯粹的品质,生活的秩序也很素朴。作为他们故事的书写者,他们也反过来影响着你?他们的生命经验中,打动你的独特价值在何处?
杨海滨:
我和他们,我们对生命的历程的感受不同。如你所说,无论是写果洛,写藏地的人,还是写郑州的故事,我其实都是在写一种生命现象,即生命的过程。我从果洛出来以后,因为看惯了生死,加上藏族人的信仰对我的影响,我慢慢变得对“生命”这个词格外看重,我感觉我写过的任何一个故事,几乎都体现了这些人对生命的讴歌。我们都是在歌颂生命。不论伤感,绝望,暴烈,那都是生命的一种现象。
镜相工作室:
您未来写作的方向会是怎样的?是继续深入,回到这片藏地,还是会更加关注自己现在身边的生活,写河南人的生活?
杨海滨:
我非常愿意继续写我的藏地往事。
我昨天到西宁来,就是约了两个老朋友,都是一些果洛人,年龄比较大了。上个月我约了一个朋友,说好这个月来跟他见面的,但是他上个月就去世了。当别人告诉我他去世了的时候,我非常遗憾,明明约好了,就要能见面了,还是没能赶上。
我还是愿意写果洛,毕竟,我还是会想到故乡给我的回忆和力量。我觉得故乡就是舌尖上的对某一个食物的深刻记忆。想起班玛来,我一定会想起那个冰凉的羊肉。我对果洛这片地方,永远都不可能忘记的,我永远愿意去写它。
当然,其实我也挺愿意关注郑州这一带的生活,主要是对一些当地的文化感兴趣。去年我采访了一个曹操墓的发现者,安阳的一个热爱考古的农民,前段时间,我还去了唐三彩的主要生产地——洛阳孟津区朝阳镇,全村63家作坊,都在做唐三彩。我觉得跟中国文化有关的内容,我还是非常感兴趣,以后我也会继续写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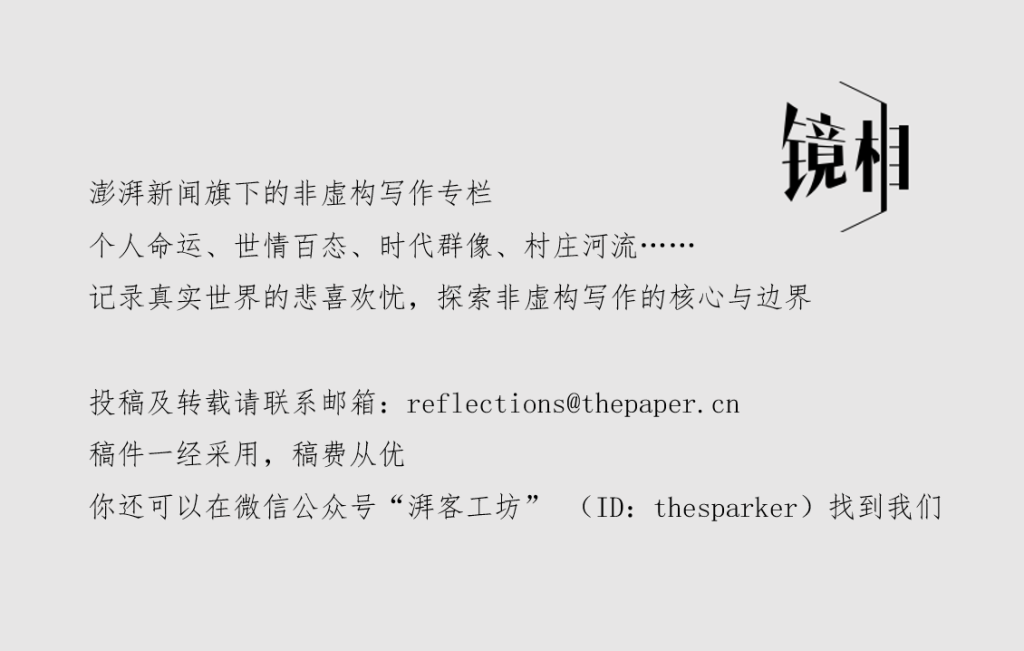
版权声明
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,不代表百度立场。
本文系作者授权百度百家发表,未经许可,不得转载。









发表评论